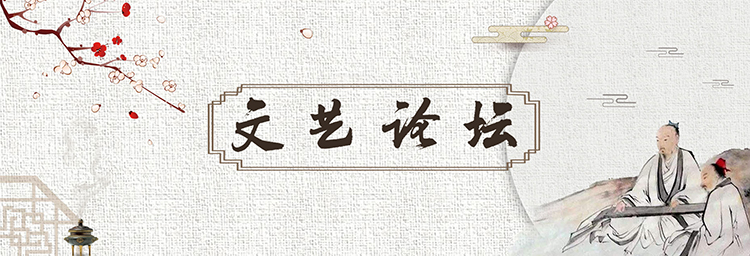

“在场主义”与自由之向
——漫谈任东华及其文学批评
文/陈雅琪
摘 要:任东华的文学批评建构可分为茅盾文学奖研究、文学评价制度研究、衡岳作家群研究三个部分,通过解读,分别对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进行了剖析,阐述了以上三部分研究如何体现了其对“在场主义”批评方法的具体实践,并指出其作为一名认真的批评家的职责和使命。
关键词:茅盾文学奖;文学评价制度研究;衡岳作家群研究;在场主义
作为一名有想法的批评家,任东华对长期关注的研究对象进行了自觉的学术建设:在理论层面,他对中国当代文学评价制度(1978—2018)进行了较为逻辑化的梳理;在实践层面,从制度、文本和世界性因素等角度,对茅盾文学奖进行了深度调研;在案例层面,他立足于湖湘精神,以八十多位衡阳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以及其他文体作家等为研究对象,构建了“衡岳作家群”这一命名。这一批评体系的建立其实是与任东华自己的学术路线相吻合的:对于茅盾文学奖的研究,起始于他的博士论文,他开创性地提出了“茅盾文学奖美学”这一概念;在更加宏观的层面上,他的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中国当代“文学评价”转型之研究(1978—2018)》对中国当代文学场域进行了详尽论述,为当代文学的整体研究提供了参考价值;博士后出站后,他回到衡阳地方高校工作,用八年的时间,收集资料,扎根于大地,对衡岳作家群进行了全面考察,展现了他作为一名地方文学工作者“绿叶对根的情意”。
一、茅盾文学奖之研究
任东华的第一部专著《茅盾文学奖研究》为他的文学评价学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与一般对茅盾文学奖的研究(多从作品角度出发)不同,任东华抓住审美性的特征,提出了“茅盾文学奖美学”这一概念,认为茅盾文学奖反映了近三十年文学的基本发展情况,形成了自己独特、开放、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茅盾文学奖美学”。他分别从制度美学、文本美学、比较美学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制度层面包括了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标准、评选过程、思想内涵、“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和“经典观”。作者认为获奖作品从题材、主潮、叙事、思维四个方面共同建构起茅盾文学奖的文本美学,特别对乡土意识、现实书写、历史叙述、现代转型等文学现象进行了解读。此外,作者还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将茅盾文学奖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进行了对比,通过文本细读分析了迟子建文学创作中的世界性因素,通过马尔克斯和贾平凹作品的相似性印证了民族书写对世界文学的意义,为中国当代文学如何更好地与世界对话提出了建设性意见。通过比较诺贝尔文学奖与茅盾文学奖,他证实了二者的深厚差异,同时也发现了这种差异中的同质性因素,即全球化时代下的一种世界性因素——各国作家对同一类型现象如何进行写作。他探究了作家在一种世界性的生存环境下的思考和表达如何构成与世界的对话,并且大胆预测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在研究方法上,他打破了学术界对“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依赖,广泛运用了接受美学、内外研究、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等,从而开创了“综合—创新”的研究方法。“综合—创新”研究方法针对“社会—历史”研究方法中“西方文论”的失语与“现实主义”研究方法的板结等弊病,遵循还原、总体性、辩证地批判等基本原则,以史料和文本为依据进行合理分析和大胆想象,侧重于探寻一种文学现象与整个时代的关系,也就是去考察相应的历史、文化语境,例如从评奖条例、评选标准、评选过程等来还原茅盾文学奖的社会历史语境。这其实也是“在场”的另一种意涵:回到历史现场。例如,在解读茅盾的八句话遗嘱时,作者通过五个关键词(“书记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最优秀”“每年”“我国”)将其放置于茅盾的创作史和百年中国文学的宏大背景下,拓展出了更为丰富的内涵。雷达对此作出高度评价:“这是一部整体性地站在文学生产制度,文学思潮起伏和审美意识发展的高度上,全面研究茅盾文学奖的具有相当分量的学术著作。”{1}
研究茅盾文学奖对于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生产制度也有着深刻的示范意义,任东华的这部著作提供了一个相当标准的研究范本。赵普光认为,文学评奖作为一种激励机制,“是一种在新的文化政治语境下实践文化领导权的积极有效形式,是党和政府通过作协等中介机构来引领文艺的具有新质的政治文化实践”。但文学评奖除了作为文学制度的重要方面对文学发展产生外部规约和导引外,也会遵循自身的规律,保持某种程度的自律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文学的自性诉求。因此,即便如茅盾文学奖这样极具政治性的文学奖项,依然会表现出其内在审美性。{2}而任东华专注于茅盾文学奖美学的研究则牢牢抓住了这一本质特性。在制度美学一章中,任东华认为茅盾文学奖的生产逻辑在于现实主义和史诗性的美学追求正好符合新时期国家民族的现代化宏大叙事的需要,与新时期文学生产的要求和政治期待一致。茅盾文学奖作为一种“国家文学”生产制度,其评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权力意志恰恰反映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和选择。在最后一章“茅盾文学奖美学的经验及未来”中,谈及茅盾文学奖的发展和创新时,任东华认可了茅盾文学奖作品中华语性、思想性、人文性的补充和加强,认为茅盾文学奖的主办者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始终在不懈地破解某些时代的、地域的和意识形态的障碍,以使中国文学完整化。我们认为,从文学生产的角度来说,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在不同时期出现的新面貌和审美特性或许能反映不同时代环境和语境下国族叙事的不同需求,以及文学在呼应制度的引力下寻求个性空间的尝试性突破和成果。事实上,从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开始,其美学风格和价值取向已经有重大转向,国家意识形态有所减弱,精神价值受到重视,纯文学作品得以凸显。具体到内容层面,对底层问题的关注,对日常生活的叙述,对中国故事的书写,无不体现了这一变化。而变化的动因和根源是什么,这一评奖价值趋向的调整与国家意识形态对主旋律文学指导空间的松动有何关联,这是一个可以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二、文学评价制度之研究
在茅盾文学奖的研究基础上,任东华自觉地拓宽了他的研究领域,从更加宏观的视角将目光聚焦在文学评价制度的研究上。文学评价学是对文学批评的制度和规律的研究,可以说是“原批评”。在任东华看来,文学批评作为独立的主体,与其内在特性、外部制度是有互文性的。对中国当代文学评价制度的研究,始于任东华对一个问题的思考:为什么同时代的批评家对茅盾文学奖作品的评价有那么大的差异?茅盾文学奖评委以拔擢当代文学经典的眼光来评价它们,而在学院派的文学史编撰中,这些作品却很少入选。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在差异中实现对话?
任东华的博士后报告《中国当代“文学评价”转型之研究(1978—2018)》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回应。该报告立足于新时期以来文学评价的独特性质、学术意义和研究现状,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和梳理,并预瞻了其未来走向。该报告致力于探讨文学评价的内在构成,作为独立的“主体”,文学评价如何与外界沟通、对话并处理与国家政治、权力的关系问题。任东华在研究方法上大胆借鉴了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对文学研究的内外划分。内部研究上,该著作归纳了当代文学评价之于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等阶段文学的核心特征;从观念、策略、方法、主体等方面对当代文学评价进行了制度层面的剖析。他还借鉴了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所提出的“文学维度”说,从文本、作家、社会、读者等基本维度出发,对当代文学评价进行了分类研究;按照从一般到具体的原则,他有机地选取了雷达、张炯、白烨、章罗生等批评家作为个案研究;同时,还对当代文学评价的现代性因素(权力、技术、焦虑、后殖民等)进行了敏锐的观察,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外部研究上,他考察了文艺政策、市场经济、文学奖、期刊(以《文学评论》为例)等外部制度对当代文学评价的影响,并用大量史料梳理了当代文学评价中的理论资源。他敏锐地抓住“转型”这一关键词,同时从外部制度和内部制度两方面讨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互联网和技术革新影响下以及西方视域审视下中国当代文学评价的发展和变化,极具在场感。
把制度引入当代文学研究,实际上是引进了一种新思维、新方法。按照福柯“话语即权力”的观点,制度即权力,作为一种政治性话语,具有自我意识,对实践主体具有指导性和支配性。制度与话语的权力本质关系体现在“制度一方面是制造和形塑话语的重要程序,另一方面,它也是话语得以对社会主体行使其支配和役使权力的保障机制,即话语‘威权’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制度的保障”{3}。当代文学制度集中体现了国家权力话语,在很大程度上规约了个人话语的生长,或者说个人话语基本是在国家话语支配下生存的。与此相似,就当代文学的性质问题,吴俊在《批评史、文学史和制度研究——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阐明:“当代文学是全方位的国家权力制度下的文学;当代任何一种文学现象、文学因素、文学流程,都要被纳入国家权力所支配的制度设计框架中。”{4}就是说,当代文学为国家意识形态所建构,是受国家权力支配的文学,研究当代文学势必要与政治权力是如何影响文学生产、传播、接受的过程联系起来,而文学制度在此环节中承担了重要作用,对当代文学评价制度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代文学是怎样被制度性设计的。
“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其实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当代文学的制度研究,即从制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这属于文学社会学的研究范畴,是外部研究;二是当代文学制度的研究,即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及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内部研究。中山大学张均和西南大学王本朝的同名著作以新时期以前(1949—1976)为研究时期,王本朝从文学机构、作家身份、文学传播、文学读者、文学批评、文学政策、文学会议等要素出发,就文学机构的组织制度、作家创作机制、文学作品发行和出版制度、读者的接受机制、文学批评制度等展开论述;张均的研究则从史料方面进行了大量佐证,并提供了一些独特的视角,比如稿酬制度的演变、制度与文人的分化、对读者的辨识和区分等,呈现出从国家文学权力机构到地方刊物,从文人作家到读者群众多层次的秩序的转移、再置和重构。不同于以上二者仅限于制度的外部研究,侧重于对史料的钩沉,任东华将中国当代文学评价制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结合起来,较为辩证地梳理了文学评价制度内在的“自我意识”的构成以及外在文学、社会场域的互动。他认为,文学评价作为独立的主体,具有清醒的反省意识,反映了文学创作的种种症候。在此基础上,他还分析了海外汉学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不同评价,这样就为找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路径提供了对话机会。而且,他的著作以新时期为起点,很好地补充了1978年至今文学评价制度研究的空缺,属于新时期以后当代文学制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衡岳作家群”之研究
在案例层面,任东华在《衡岳作家群研究》一书中,首先总体性地梳理了衡岳作家群的研究缘起、生成文脉、建构科层和美学形态,然后对衡岳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别种文体家进行了发现。有意思的是,任东华没有选择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而是选择由无名作家以点带面铺开呈现了本土文化的丰富和个性;本着扎根土壤的艺术原则,他还进行了大量广泛的田野调查和史料收集,为衡岳作家建立了乡土档案并进行了史料汇编,这无疑是具有奠基意义的。
此外,从区域文化的视角来研究作家或作家群现象也有其内在意义。环境,在美学家泰纳那里是被当作与种族、时代并列的文学三要素之一。他认为,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都对文学有重要影响。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里强调并推崇“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将浙江文艺的风土特点总结为“飘逸与深刻”。他认为,人是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5}。任东华将衡岳作家的特征归纳为自省和坚守,并提出“文学土壤学”的概念,暗合了周作人的这一理念。他在其著作中特别谈到了“文学土壤学”的发微。任东华认为,无名作者才是伟大作家诞生的群众基础。他进一步归纳,“文学土壤学”是指构成中国当代文学基本存在形态的“底层”部分。无名作家作为“文学土壤学”的本体构成,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他们人数众多,无比钟情于文学,没有任何功利心理;第二,他们处于读者与著名作家、文学大师之间,成为其间不可或缺的纽带;第三,他们的遭遇,呈现了文学在地方的生态基因;第四,他们的意义不在于本身的文学成就,而在于他们孕育了文学的无限可能性。{6}特别是在当今经济和文化都被同质化的全球化时代,地域性正被逐渐冲淡和遗忘,正如雷达所言:“坚守文化的地域性、文学的本土化,致力中国经验的深刻表达,包括小到研究‘区域作家群现象’,无疑具有深刻意义,这也是保持世界文学的多元性和丰富性的重要途径。”{7}
任东华认为,由于地理因素和文化环境,衡岳文学被深深地打上了湖湘文化的烙印,有着厚重的道统、学统和文统。源于这些伟大的传统,衡岳作家群形成了这样几个科层:一是衡籍外域作家,二是外籍衡域作家,三是长期扎根于本土的作家,四是其他与衡阳有关联的作家。从文体而言,包括小说家、诗人、散文家,以及乡土杂文家、寓言家、戏剧家、网络写手等别种文体家。从美学形态而言,呈现了对现实的省视、对历史的反思、个体情感的现代书写、乡土诗意的激情迸发、艺术的坚守与突围等形态。{8}该著作的独特之处在于对衡岳作家群的研究,以探讨作家群体共同的文化命脉和主体精神为主,重点分析其作品如何承接了湖湘文化传统,又是如何与沈从文、周立波等文学大家相衔接的。这恰恰反映了任东华在“文学土壤学”中对无名作家的定位——连接读者与文学大家的纽带。比如,他在该著作中分析了彭绍章的小说,认为“它表达了扩散在平凡人身上的时代苦闷和精神荒芜,直追赵树理的山药蛋派”{9}。除了归纳衡岳作家群的生成文脉和美学形态,他还分析了当前群体创作的症候和病灶,指出其局限性和如何应对这一危机。总体来说,该著作以资料收集为基础,辅以文本分析、作家访谈等方式,不仅全面反映了衡岳作家群的创作形态,而且广泛汇编了衡岳作家群的其他研究资料,在地域作家群研究的文学版图上构成了不可或缺的“一隅”。
在即将出版的新作《批评的在场》中,任东华将自己的研究方法总结为“在场主义”。“‘在场’就是直接呈现在面前的事物,就是‘面向事物本身’,就是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因此,‘在场主义批评’所强调的‘在场’和‘批评性’追求就是‘去蔽’,就是在与黑暗的主动接触和冲突中,通过无遮蔽的敞开,而达至自由之境。”{10}该著作彰显了他对“在场主义批评”的推崇和实践。“在场主义批评”所主张的介入包括:对作家主体的介入,对当下现实的介入和对人类个体生存处境的介入。结合任东华的文学批评实践,他的“在场主义”批评具体表现为:在茅盾文学奖研究中运用还原原则,即把茅盾文学奖还原到它所产生的历史情境和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情境中;在文学评价制度研究中运用总体性思维模式,即从有关研究现状、意义和方法到研究对象的内部研究(特征、分类、案例文本)和外部研究(理论资源、制度),最后到问题和启示;在衡岳作家群研究中运用历史性视角,即在解读作家作品时将其放入文学的时代潮流或地域特征中去。通过发现问题、建构理论,避免片面和局限于内部,他对相当一部分文学现象和作品进行了“去蔽”的发掘,打扫那些“隐形”事实上的尘埃,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这恰恰是“在场”的意义所在。
其实,无论是对文学作品的重新阐释,还是对文学史的再度发掘,亦或对文学现象的重新考据,都不是为了推倒既往的事实,而是要对已成为共识的东西进行“去蔽”,在多方面的对话关系中挖掘未发现或被遮蔽的意义,纠正偏颇的评价。在此意义上,批评家的使命不仅仅是解释,还有戳穿事实的重任。
任东华的批评大多客观中肯,以详实的事实材料为依据,不妄自下结论。正如他自己所言,不因自己的钟爱而过度溢美,不因自己的憎恶而竭力棒杀。这是一位认真的批评家最基本的职业素养,也是任东华一直践行的批评理念。
总结任东华的学术路线(实践—理论—案例),我们发现,他始终遵循着从一般到普遍再到个别、由现象到本质再到表象、从中观到宏观再到微观的规律,来有意识地建构他的学术追求。如果把理论比作根,实践就是根茎之上生出的花,而案例则是滋养着它的土壤和肥料,三者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沿着这条学术小径,我们可以见证一位基层批评家的成长以及他在学术研究领域的自觉探索。
注释:
{1}任东华:《茅盾文学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2}赵普光:《文学评奖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制度的重建》,《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2期。
{3}王馥芳:《话语“威权”主要源自制度的保障》,《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12日。
{4}吴俊:《批评史、文学史和制度研究——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若干问题》,《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4期。
{5}周作人:《谈龙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6}{7}{8}{9}任东华:《衡岳作家群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5页、第8页、第23—24页、第51页。
{10}任东华:《批评的在场》,湖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
(作者单位:bet356手机版唯一官网登录文学院)
原文链接:https://moment.rednet.cn/pc/content/2021/04/06/9158317.html
 欢迎您访问bet356手机版唯一官网登录网站!今天是:
欢迎您访问bet356手机版唯一官网登录网站!今天是: 欢迎您访问bet356手机版唯一官网登录网站!今天是:
欢迎您访问bet356手机版唯一官网登录网站!今天是: